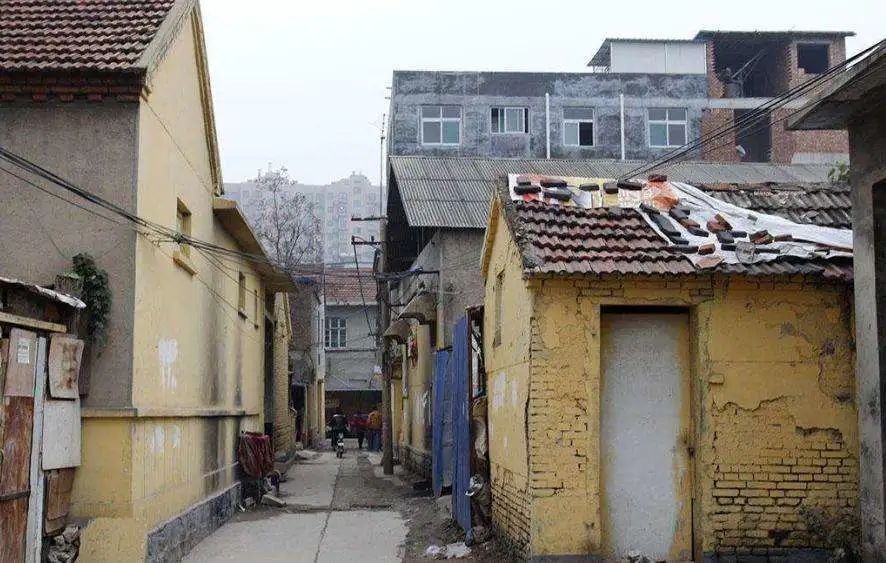|
【以案說法】城中村改造案件裁判規則20則(干貨總結)【以案說法】城中村改造案件裁判規則20則(干貨總結)編者按:城中村改造案件紛繁復雜,審理難度較大。小編對近年來法院審理的涉及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案例和常見問題進行了梳理匯總,分享給大家,案例觀點僅供參考學習,實踐中遇到類似問題還是要結合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1.城中村改造行為與土地征收行為的區分 【裁判規則】(1)從表現形式看,被訴城中村改造行為主要是行政機關為推進城中村改造,對相關土地權利人進行搬遷安置,并通過簽訂協議的方式處分了集體土地上房屋,但土地性質仍然屬于集體所有,并無證據顯示集體土地已被批準征收或者有關部門已啟動土地征收工作。(2)從訴訟請求看,行政機關推進實施的城中村改造行為,實際上包含了簽訂協議、補償安置、拆除房屋等一系列行為,涉及多個主體、多個環節,當事人籠統地起訴“征收行為違法”,屬于訴訟請求不明。(3)從權利救濟看,雖然根據在案證據難以將被訴城中村改造行為界定為行政征收,但作為影響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仍應接受司法審查,人民法院可依法作出合法性評判。因此,當事人可就上述城中村改造所涉的補償安置協議、房屋拆除等行為依法提起訴訟。——(2019)最高法行申10221號 2.城中村改造并不必然以征收集體土地為前提 【裁判規則】目前在法律程序設計上并不存在獨立的征收集體土地上房屋的環節,通常是在征收集體土地過程中將房屋納入地上附著物補償范圍。城中村改造并不必然以征收集體土地為前提,且已于2019年8月26日修改、將于2020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就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等又作出新的規定,集體土地領域的管理今后將更加靈活、多元。整體上看,如果不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地方政府針對城中村改造依法具有一定自主管理權;如果需要改變土地所有權性質,則必須依法由省級以上人民政府審批。——(2019)最高法行申10184號 3.籠統要求確認城中村改造行為違法,屬于訴訟請求不明確 【裁判規則】當事人請求確認城中村改造行為違法,但并未明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是征收、征用決定,補償決定,還是其實施的行政強制措施、行政強制執行等行為,其訴訟請求不明確,提起訴訟不符合法定條件。——(2019)最高法行申13063號 4.城中村改造項目批復是否可訴? 【裁判規則】(1)行政機關作出的不具備法效性特征的行為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法效性是指行為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所謂直接,是指法律效果必須直接對相對人發生,亦即行政行為一旦作成,即導致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消滅。所謂對外,是指行政行為對于行政主體之外的人發生法律效果,行政機關之間或行政機關內部的意見交換等行政內部行為因欠缺對外性而不具有可訴性。(2)一般來說,城中村改造項目批復,雖然涉及了城中村改造的有關內容,但其是針對有關單位的內部審批行為,未直接設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對其并未產生實際影響的效果,其法律效果還須通過有關職能部門依職權針對特定相對人作出相應處理決定加以實現,故該批復不具備直接、對外發生法律效果的特點,不具可訴性。也就是說,在城中村項目實際改造的過程中,相關行政機關作出的征收、安置補償等直接設定當事人權利義務的行為才產生直接對外的法律效果。——(2018)最高法行申1466號 5.城中村改造方案批復是否屬于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方案批復系根據地方性文件的規定,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改造方案的內部審批行為,并不直接對外創設權利義務,僅系整個城中村改造的一個程序性環節。對當事人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的是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的拆遷安置及補償行為,當事人如對安置補償行為不服,應直接針對安置補償行為提起行政訴訟。城中村改造方案批復一般不屬于行政復議的受案范圍。——(2016)最高法行申4469號 6.城中村改造實施方案批復一般不具有強制拆除房屋或征收宅基地的效力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實施方案批復一般是行政機關針對村集體自主確定的改造范圍、改造模式等內容所進行的確認,該批復本身并不具有強制拆除房屋或征收宅基地的法律效力,未實際影響當事人的權利義務。——(2020)最高法行申6862號 7.政府作出城中村改造批復能否視為實施強拆行為的委托 【裁判規則】政府作出同意下級行政機關實施城中村搬遷改造的批復,如果在下級行政機關的請示或政府的批復中,不包含組織拆除的時間、對象、拆遷工作人員等內容,則該批復僅是決定對城中村實施搬遷改造,不能將該批復視為上級政府對下級行政機關實施的強制拆除行為的委托。——(2020)最高法行申7570號 8.城中村改造責任主體的確定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拆遷安置補償方案中明確有關行政機關負責組織實施拆遷補償安置工作。并且,當事人提供的證據也說明城中村改造系由行政機關主導進行。雖然補償方案中規定,相關民事主體為整村改造的拆遷主體,但由其不具有拆除房屋的職權,故其實施強制拆除房屋行為應視為受行政機關的委托,相應的法律責任應由委托機關承擔。本案中,政府對街道辦呈報的城中村改造拆遷安置補償方案作出批復,同意該方案施行,并批復街道辦接文后,認真組織實施拆遷補償安置工作。政府的上述批復行為,系其行使相應行政管理職權的行為。雖然補償方案中規定,集體經濟改制成立的公司為整村改造的拆遷主體,該公司亦認可其實施了拆除當事人宅基地上房屋的行為,但由于其不具有拆除房屋的職權,故其實施強制拆除房屋行為應視為受行政機關的委托。13739號——(2019)最高法行申13739號 9.城中村改造適格責任主體的認定,不能僅憑村委會自認判斷強拆責任主體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適格責任主體,應當結合當事人提供的視頻、錄音、照片等證據,以及城中村改造資金來源、城中村改造后土地歸屬、行政機關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的作用等因素進行全面審查和認定,而不能僅以村委會的自認進行判斷。本案中,城中村改造實施意見規定,城中村改造采取政府主導、村集體自我改造、市場運作的模式進行改造。拆遷方案上有行政機關署名并加蓋公章,改造過程中有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參與,改造資金來源于土地出讓金。基于此,雖然拆遷方案中規定村委會是實施主體,其也承認實施了拆除當事人房屋的行為,但由于其不具有強制拆除他人房屋的職權,故其實施強制拆除房屋行為應視為受行政機關的委托,相應的法律責任應由委托機關承擔。——(2020)最高法行申5250號 10、11.村委會組織實施的強拆活動,需要根據在案證據明晰是否存在行政委托還是單純的村民自治組織的自主意志 【裁判規則】實踐中,對于村委會組織實施的強拆活動需要明晰是否存在行政委托還是單純的村民自治組織的自主意志。無論哪種情形一旦存在不法侵權,被侵權人有權依照法定途徑尋求救濟。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在案證據指向村委會組織實施了城中村拆遷改造,并不足以證明由被訴行政機關組織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故從目前在案證據難以認定被訴行政機關為強拆行為的責任主體。——(2020)最高法行申2732號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發生的強拆行為,現有證據均指向村委會,尚不足以證明被訴行政機關參與。本案被訴的強拆行為系事實行為,長安區政府在一審階段提交的《長安區西兆通鎮東兆通城中村改造拆遷安置補償方案》《拆遷清包工實施協議》《西兆通鎮東兆通村委會通告》《東兆通村關于拆遷問題的情況說明》以及《東兆通村民代表召開舊村改造專題會議》等證據,能夠證明該強拆行為并非長安區政府直接實施。同時,申請人提供的證據并不足以證明長安區政府對涉案房屋實施了強制拆除行為,其起訴缺乏事實根據。——(2020)最高法行申2734號 12.村委會在簽訂拆遷補償協議后實施房屋強制拆除的情形 【裁判規則】原告起訴被告實施行政強制拆除行為,應當提供證據初步證明被告實施相應的行政強制行為。如果不能舉證初步證明,甚至有相反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根本未實施被訴的行政強制拆除行為,則起訴沒有事實根據,不符合法定起訴條件。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當事人就案涉房屋與所在村委會簽訂搬遷協議,明確約定搬遷時間、補償標準等,并按照協議約定領取補償款,涉案房屋被村委會組織人員和設備拆除,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初步證明涉案房屋強制拆除行為系被訴行政機關實施。——(2020)最高法行申4872號 13.城中村改造中的拆遷行為不宜假借村民自治形式進行 【裁判規則】在現行土地和房屋征收補償法律法規框架內,基于“舊城改造”“村改居”或者“新城鎮建設”等實際需要,村民會議或者村民代表會議可以在符合上位法規定前提下,通過村民自治方式決定建設項目和補償事項,并可通過簽訂協議等方式解決補償安置問題;但在未經協商一致情況下村民委員會等自治組織即單方采取強制拆除等方式則涉嫌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等法律法規,對強制搬遷合法房屋的步驟、程序和方式有具體明確的規定,并未規定村民委員會等自治組織有權實施強制搬遷和強制拆除。——(2019)最高法行申3801號 14.城中村改造中簽訂拆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效力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是介于集體土地征收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行政行為,更多的側重于事實行為和政策性文件的支持,實質上是法律規定不完善情況下對城市建成區范圍內集體土地進行改造、建設的一種探索和改革行為,這種行為在總體上有利于原住居民的財產增長,有利于推進城市建設,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也因此,對于此類行為的審查,往往缺乏法律法規依據,更多的是合理性審查,而不是合法性審查,只要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不侵犯公民的重要財產權,就可以不受法律優先及法律保留原則的限制。——(2019)豫行終1104號 15.能否以未作出征地批復為由撤銷拆遷過渡協議 【裁判規則】拆遷過渡協議屬于行政協議的一種,對于行政協議的合法性審查,在不違反行政法律強制性規范的情況下,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規范。簽訂拆遷過渡協議目的是落實城中村改造工作,協議內容為房屋拆遷、過渡事宜,其約定的過渡費、搬遷補助費等標準亦在合理范圍之內,不存在法律規定的可撤銷的情形。拆遷過渡協議簽訂時,行政機關雖未取得征地批復,但征地批復是否作出并不影響當事人對其權利義務的認知,不屬于合同法規定的重大誤解、顯失公平以及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等可撤銷的情形。——(2018)最高法行申5439號 16.拆遷安置補償協議的效力否定 【裁判規則】在不履行行政協議職責案件中,行政協議是當事人要求行政機關履行法定職責的依據,行政協議是否合法有效,是判斷行政機關是否應當履行行政協議的先決問題。對行政協議效力的判斷,要結合行政訴訟法及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對重大公共利益、契約的安定性、形式上的依法行政、當事人的信賴利益等價值進行利益衡量,在各種價值之間取得相對平衡。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行政機關與被拆遷人簽訂拆遷安置補償協議時適當突破有關規定,提高給予被拆遷人的補償標準,從維護契約自由、維持行政行為的安定性、保護行政相對人信賴利益的角度出發,可以認可行政協議的效力并要求行政機關予以履行。但補償協議中給付標準明顯突破了法定標準、行政相對人故意隱瞞真實情況或偽造虛假材料簽訂協議獲取不正當利益、行政協議的基本依據虛假,履行行政協議會給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損害的,則不宜認可協議效力并要求行政機關履行。——(2019)最高法行申5940號 17.城中村改造中的拆遷通告是否可訴? 【裁判規則】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如果拆遷通告徑行規定了拆遷范圍、要求停止生產經營、規定期限內搬離拆除現場等內容,對被拆遷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了實際影響,具有可訴性。——(2019)最高法行再34號 18.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的房屋拆遷安置實施方案通知不可訴 【裁判規則】在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如果行政機關發布的房屋拆遷安置實施方案通知及所附的實施方案均沒有強制實施的相關條款內容,行政機關也明確表示該方案不具有強制執行力,當事人不同意簽訂房屋征遷安置協議,政府不會對其實施征遷,則該通知及方案不產生強制力,一般不具有可訴性。——(2019)最高法行申13732號 19.村民通過自治程序形成的拆遷安置補償方案的行為是否可訴? 【裁判規則】“村民自治”模式下城中村改造行為的性質,應當綜合考慮拆遷補償方案的實際制作主體、實際補償主體、政府的參與程度、土地改造后的用途等情形來加以確定。如果拆遷補償方案的實際制作主體、補償資金的實際支付主體、最終的用地主體或受益主體以及實際的拆遷實施主體均是政府及有關部門,則應當認定該行為超出了村民自治行為的范圍,有逃避征地批準法定程序之嫌,相關行為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2018)最高法行申1614號 20.在未簽到補償協議的情況下,以“拆違”促“拆遷”屬濫用職權 【裁判規則】城中村改造過程中,因拆除被征收人房屋而發生行政爭議。由于農村發展程度及行政管理的實際情況等,農村集體土地上房屋普遍存在著只有部分建設手續甚至完全缺乏建設手續的情況,這是一種客觀現實,不是農村居民能夠克服和解決的,其不存在過錯。相反,這種管理現狀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機關造成的。行政機關在當事人未簽訂拆遷補償協議的情況下,不遵循法定的組織實施程序,徑行將被拆遷人房屋認定為違法建筑并強制拆除,其執法目的不是為了嚴格農村土地的管理使用,而是為了避開法定的組織實施程序、加快拆除進程,屬于濫用職權行為。——(2017)豫行終2450號 |